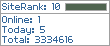八十年代的大陸,馬路清凉,物質貧乏,可從那時過來的人都懷念。那到底是哪般滋味,任人怎麼口述也無法體會。他們說那時純潔,也說那時理想化,一窮二白,人卻帶着本真。看着任曙林當日鏡頭捕捉的,是否讓不曾在那年頭、那地方走過的你,抓得住那無處尋覓的滋味?撰文:鞠白玉圖片由被訪者提供
放大圖片 
81年,任曙林。
任曙林,知名攝影家。 54年生於北京,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攝影系及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, 76年開始師從狄原滄學習攝影,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先鋒––「四月影會」的重要成員。幹過八年維修鉗工,拍過十餘年科教電影,代表作:《 1980年的北京高考》、《中學生》、《妻子》等。近年多次於國內外舉辦個展,現為中國攝影家協會及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員。他曾說,攝影是上帝交給人類的最後工具,所以他好好珍惜着。不過他從不說想給後來的人留下點甚麼,他說他自己過了癮。「攝影真不是大不了的事。我想有一天,我這書房裏再也沒有一本關於攝影的書,我把相機也會賣掉。我也再不談論這些。我就坐這屋子裏面喝茶就行。」
放大圖片 
■ 84年,坐在 171中學的籃球架下的任曙林,也散發着一個時代的氣息。
北京深冬雖然蕭瑟,他卻每年都養着幾盆室內的花,放在小窗台上受着日照,精心照料它們的綠葉子。書房簡陋,除了書本,只有兩個對坐的沙發和木茶几,式樣都是八十年代的。地板顏色用白和綠調和,別人家都不再有的顏色。室內放着一輛黑色 28式自行車,在北京的街上也鮮見了。他的衣着舉止,他的鏡頭所及,依然帶着八十年代式的純粹,這公寓也是他曾經供職的煤炭部門分的公房,社區裏的氛圍也顯得和現代的北京那麼格格不入,像是有心和這時代拉遠一點的。他說:這一切都挺好的,真的挺好,我只是做我的事。
放大圖片 
任曙林於八十年代,以北京 171中學為主拍攝地所記錄的中學生影像,最近於《八十年代中學生》音樂影像展中重現。
放大圖片 
當它們是相對着,就像延伸出許多故事……
放大圖片 
他們在限制中尋找着自己的空間……
放大圖片 
25年前的中學生,每天要清潔教室,擦窗是最日常的一幕。
放大圖片 
放大圖片 
放大圖片 
放大圖片 
放大圖片 
不是使命是喜歡
他也從來不去那些大山裏,高原上,不去擷取自然的風光,不去吹那凜冽的風。他只是拍他所能看見的人,中學裏的年輕人,或者他的妻子,他的兒子。他每拍一次都覺得和他們更近了一些,更瞭解了一點,他通過拍攝重拾自己的記憶,驗證一些生活裏的本質。任曙林無法接受那些試圖用艱苦來證明自己的攝影作品,他看不得人為了鍾愛的事情受苦。他的理想狀態是「喝着酒,唱着歌」就把事情做完了。背負着責任感使命感的事情,讓他覺得全無純粹,所有事情的出發點,在於他自己喜歡。他身上帶着一種玩世氣,又時而正色起來。談到攝影,他時常在公開場合貶損或炮轟,他有自己的體系,他說攝影是用第三只眼,又說攝影不是用腦子的,是用直覺,用心。他曾是官家子弟,父親曾是商業部長。這使他在八十年代有機會得到一台相機,他是「四月影會」的成員,但也是那沙龍裏的叛逆者。別人都着迷於大型的風光,他卻老想找一些人群裏的隱秘,那些平凡世界裏值得珍惜的東西。三十五年前他登京西的妙峰山,隨手拍一張大全景,古塔下的年輕學生在眺望交談。後來他對那情景念念不忘,他不知道到底是那古塔吸引他,還是那些年輕的身影。知道有種神秘的東西早晚指引他去某個地方。
跟日本同樣愛以妻子作拍攝對象的荒木經惟相比,他的作品,更有一份尋常百姓的味道。
放大圖片 
我只不過把《妻子》當做窗戶和鏡子,
放大圖片 
我想看到些甚麼,
放大圖片 
發現些甚麼。
放大圖片 
放大圖片 
放大圖片 
透明影子記下「青春」
《中學生》系列有着歷久彌新的力量,他始終說不清自己當時為甚麼要拍攝他們,現在他說:因為我愛他們,她們。「我試圖去尋找舊日的時光,那些我現在無法企及的地方。」看這二十幾年前的畫幅再次展出,從色彩上能看出夢幻,像是一個人的青春夢,緩緩地刻下了。她們全都清瘦,有精緻的腳踝,細長的身形,多數穿着校服,只有髮梢上纏繞着的蝴蝶結在偷偷地,低調地顯着不同。一模一樣的軍綠書包,在操場的樹下堆放着,她們的主人在歡騰跳躍,在打發着時光。她們時而顯得無憂無慮,時而無處訴衷腸。很多少男少女的秘密,在底片中埋藏。那年他進入北京 171中學,年輕孩子都叫他叔叔。這叔叔經常將褲腿挽起,像個漁民,手裏持着膠片相機。起初他們都躲閃着,當他是記者,直到每時每刻這人都無聲地出沒,他們才將鏡頭視為這是日常生活的部份。「他們在限制中尋找着自己的空間,這是他們生存的必須。在課後自己的天地裏,這恰恰是攝影進入他們的通道,他們的廬山真面目,一點點地留在底片上。」那時他們與她們都別樣的含蓄,他知道一定有許多愛情故事在這校園裏發生,卻看起來毫無影蹤,他像在看一幕幕青春話劇,他成了一個透明的影子。那男生和女生在窗前佇立,默默無言,好像是只要靠得夠近,就算做交流。他拍許多男生女生的背影,拍他們的腳踝和鞋子,當它們是相對的方向,就像延伸出了許多的故事……太久遠了,當年那些孩子的情愫不知他們自己還記得否?
強烈的性意識
拍攝《中學生》時他還在國家部門任公職,常要出差工作。但每次回京又急急背着相機進入校園,體會其中的細微的變化。時光流淌,總有些甚麼注定是無法留下的。他總覺得八十年代的年輕人更好看。目光清澈臉龐潔淨,「那是真正的單純爛漫。」他記得在操場上遇到的一對少男少女,他們趕着回家,天空下着雨,男的伸出手放在女的頭頂上,那樣一隻手並無法擋住雨滴,但是他在盡力。他們無法相擁摟抱在一起,卻是這樣小小的舉動演繹着純愛。「現在能見到的中學生,可以旁若無人,他們在馬路邊上糾纏成一團,熟練地牽着手,卻再沒有那個年月的美感了。」情懷暴露了他的出處。但凡懷念過去的人,是因為過去之於他,是生命裏的黃金時代。這些年他獲獎,辦展,在北大講座,他的精氣神的出處卻都在從前。那些年他所目睹的青春劇情,就像根植在腦海裏。他想,不是因為他懷念八十年代,是因為他永遠懷念年輕。他自己就像個守望者,永遠想守護那些少年人。有一年陳丹青為他寫評論,其實兩人素昧平生。他給任曙林打電話,第一句話便問:你說你當時拍的時候是不是有很強的性意識在裏面?其實他這些年也一直在尋找當日的線索。一語中的,他承認了。
告別的一刻 放大圖片 
■ 11年,北京街頭的年輕情侶。
今天,「中學生」都老了。他作品裏的一個主人公,現在恰好當了那所學校的校長。前幾年他們重新聚首,和這個當年的「叔叔」一起吃飯。他們和她們也是中年人了,也不知道自己當年那麼美。 87年以後,他停止了這題材的拍攝,他知道最好的時候已經過去了。 89年 6月的下旬,他去了頤和園,悵然若失,看着園裏有幾個大學生在跟着錄音機的音樂跳舞。他偷偷拍下這個場面,從此和青春夢作別。
放大圖片 
鞠白玉,滿族女,八十後,達達主義者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