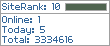人生本無常,二○○一年美國發生「九一一」恐怖襲擊,韋家輝身在美國,「老闆請我們去拉斯維加斯,入住的Villa窮奢極侈,周圍的客人畀貼士都是幾十元美金。」
「無論作品有多天馬行空,一定與生命出現過、相關的東西刺激你才諗到,不可能無中生有。」他說。
宗教、哲學等課題首次在他生命中出現,是黃大仙,他是「黃大仙契仔」,「我農曆生日是黃大仙誕,阿媽契咗我畀黃大仙,屋企會拜觀音,過年一定跟阿媽去黃大仙廟。」
探索無常
韋家輝愛思考探索,小學已獨自到圖書館看書,「我對兒童圖書館無興趣,覺得成人圖書館的書有趣一點。」他愛看科學書,有關恐龍如何絕種、地球是怎樣形成、近視能否治癒等課題的書,他愛不釋手。
家中有四兄弟姐妹,他排行第二,胞弟是演員韋家雄(《真情》裏的「大力」)。「人生無常」很早在他生命中出現,十歲左右,爸爸突然離開屋企,「他上大陸做生意,有另一個家庭,好瀟灑地一個人走了。」
父親原本開塑膠廠,家境不俗,「以前有私家車,突然間屋企好窮,無咗個爸爸,成日見到唔開心的媽媽坐着發吽,會諗好多嘢,想幫她分擔。」人生哲理,慢慢在韋家輝體內萌芽。
大時代
應徵既要投稿又要面試,被問對當時熱播的劇集《上海灘》有何意見,「我返工無睇過,只對預告片有印象,所以說:『那時上海不是這樣的吧?』」見他的其中一人,正是《上海灘》編劇梁健璋。
「他說請我與否只是一念之間,因為我是marginal的一個,其他人的學歷都比我好。」當時無綫編劇訓練班幾個月一期,每期要請五個人,韋家輝成為那期第五位入職的員工。
入職後,他嶄露頭角,為期半年的訓練班未完,梁健璋就把他抽調出來幫手寫《飛越十八層》,連課堂也不用上,「他是第一個發現我有創作天份的人,我提出的都用在劇本上。」
「當年編《流氓大亨》,大結局在周六、日播,我去媽媽屋企食飯,走的時候聽到全個屋邨響起主題曲,然後很多人一齊落樓走,你就知道很多人睇埋自己套戲先肯走。當一樣嘢hit,真係feel到。」他帶點自豪地說。
「八九民運令我很激動,很想拍有關文革的劇集,恰巧林建岳去了亞視,有彈藥挖人。」他過檔的條件是要拍文革題材,拍了《還看今朝》,收視達廿七點,創亞視的收視紀錄。
他更改寫電視台的運作模式,容許「飛紙仔」,即臨入攝影棚才出劇本,「老一輩都是返朝九晚六,我們卻帶頭組成夜晚的創作小組,累了瞓椅子,天光就刷牙,睇住其他同事相繼上班。」
「是騎虎難下,我們不是去玩唔交稿,個個通宵度劇本,做到成隻殭屍咁。」無綫內外的同行都知道他的瘋行,影帝周潤發把他拉入電影圈,「是時候了,唔同周潤發拍,他就要去荷李活。」
「有人話我的戲唔正常,有些則說布局複雜到傻,甚至話我是傻的。我覺得好正常,有時嫌它不夠複雜。」他的作品最初不太被觀眾接受,到外地影展走一圈,好評開始出現,影評人也漸漸喜歡這種「另類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